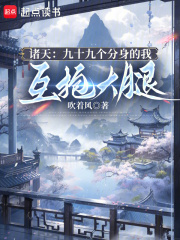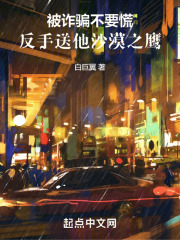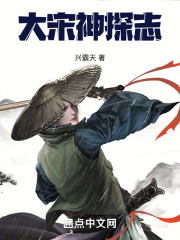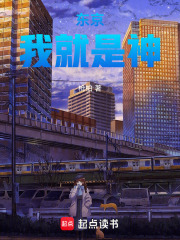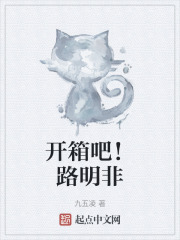东北大老李原创:大巴及绿皮火车
昨日整理旧物,发现一张旧时的纸板火车票,出发站大巴,终到站沈阳北站。
大巴是一个镇,离我家二十里地,也是我儿时仅次于县城的繁华之所。
记忆中的大巴,那里有周边二三十里范围内的最高的建筑——二节楼。
二节楼在大巴中心区,是一个商场,在它的二层西南角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照相馆,那也是附近人们有个大事小情,需要拍照留念时必去的地方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附近十里八村的年轻人照结婚照,更是非那儿莫属,除此之外,照相馆日常也会为学生和公职人员照些一二寸的证件照。
照相馆里的师傅轻易不会带着金贵的照相机外出照相,一来别处没有照相需要的各色灯光和布景,二来也没有那么多人手和相机,但凡事总有个例外,那就是赶上暑期各个村的小学毕业,里面的照相师傅也会应约带着照相设备,到各村小学,给孩子们照毕业像。
由于照相馆的师傅一年来一次不容易,此时也常会有附近的村民携家带口来照张全家福,记忆中,那时的照片全是黑白的,我家也曾照过几张,印象最深的一张,取景是小学校门口的几棵小柳树,明媚的阳光下,笑意盈盈的父亲和母亲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,母亲抱着两岁围着折巾儿的弟弟,五岁的我则眯着小眼睛站在旁边。
大巴除了二节楼的商场和照相馆,那的集市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,尤其是赶上年节的大集,更是人声喧闹,摩肩接踵,套用歌词来说,有上学用的笔记本,铅笔、钢笔、文具盒,有姑娘喜欢的小花布,小伙扎的线围脖,秋衣、秋裤号头儿多,又可身来又暖和,小孩儿用的吃奶的嘴儿,挠痒痒的老头儿乐,……,当然了,做为农村特色,也有各种锹、镐、犁杖等农用五金产品,再有一个就是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,应季的瓜、果、梨、桃,以及豆腐、粉条,牛、羊、驴、猪、鸡肉及下货,此外,还有冻鱼虾皮等水产,可谓应有尽有。
要说儿时对大集印象最深的地方,就是那些让小孩馋的哈喇子直淌的各色吃食儿了,糖球儿,奶豆儿,炉果,麻花,油条,槽子糕,冰棍儿,……至今想来,嘴里都是水津津的。
大巴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有一个,就是在它的西北角有一个火车站,那也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。
说起那时的大巴站,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场所,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那里的火车不但通着灯红酒绿的县城,更通着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地方——新立屯。
上初三前我从未坐过火车,至于见到火车,似乎早一些,记得那一年,二姨和二姨夫去大巴照结婚照,五岁的我愣是连哭带喊地蹭着他俩的自行车去了一趟大巴,也就是那次,在街北道口,一列不知有多少节的绿皮火车拉着响笛,轰隆隆地开过,自那以后,我才知道除了不常见的汽车,还有比它更高级的火车。
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上初三那年,我和我英语老师去县城参加英语演讲比赛,从大巴向西坐三站到县城的阿金站,自那以后,我坐火车似乎也就多了起来,尤其是九十年代,我来到沈阳以后,火车便成了我回老家必选的交通工具。
九十年代,从大巴站到沈阳站(后改为沈阳北站)有早晚两趟火车:
一趟是上午九点多,到达沈阳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左右,还有一趟是晚上五点多,到达沈阳时间是晚上八点左右。
从沈阳到大巴的火车也有两趟:
一趟也是上午九点,到达大巴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左右,还有一趟是中午十二点多,到达大巴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多。
那时沈阳到大巴的区间票价好像是十二元,对于这些,我的记忆确实有点模糊,但说起当时的车站,至今仍是十分清晰,从县城的阿金到我上车的大巴,再到沈阳,有下列这些站点:
阿金、新邱、沙拉、大巴、后官山乘降所、苍土、新立屯、泉眼、小东、老民屯、姚堡、小梁山、贾家乘降所、杜屯、罗家、高台山、巨流河、兴隆店、三台、MA三家、沈阳西、大成、皇姑屯和沈阳。
当时大巴火车站真的很热闹,黄墙门脸,门楣上水泥套刻的黑边白站牌,“大巴”二字更是格外显眼。
大巴火车站的票房子不大,到了要发车的时间,总会挤挤压压地站满了人,有接站的,有送站的,有买票的,有退票的,还有改签的,由于都是十里八村附近住着的人,大家平时就是熟头巴脑,那交流也自然亲切了很多,他们大声说笑着,连打带闹着,总是一副开心的样子,至于说女人们穿着出门才穿的好看衣服,男人们抽着出门才揣的洋烟卷,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了。
票房子里热闹,外边也清静不了,沿墙根儿有卖各色吃食儿和卷烟的小摊,他们总是不停地哟嗬着,至于说那摊儿上的东西,什么花生、瓜子、方便面,什么汽水、饼干、茶叶蛋,更是应有尽有,这边哟嗬着,那边送站拉车的驴儿有时也会不安分,常会引吭呕啊——呕啊——呕啊啊——地叫上几声,至于说赶上专业送站的驴车会面,看自家主人与另外几位正相互打着招呼,驴儿们也会此起彼伏地再呕啊啊——呕啊啊——地叫上一番。
说到接送站,平头百姓多坐小驴车,至于说有钱的人家,也会开着声响极大的摩托或是小蹦蹦儿,一到站外,司机们有时也会张扬地拧上几下把线儿,让那些家伙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地喷上一会趾高气扬的白烟儿。
大巴到沈阳的火车是标准的绿皮火车,前边说过,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,大小站点就有二十多个,平均不到十公里就是一站,由此看来,火车三个多小时还跑不到二百公里,也就很好理解了。
绿皮火车上印象最深的是往来叫卖的售货车,扁扁长长的四轮手推车,里面装着各种好吃的吃食儿,工作人员叫卖声也是悦耳:
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啦,花生、瓜籽、烤鱼片啦……
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带有浓重乡音的列车广播:
各位旅客请注意,前方到站是XX站,有下车的旅客请带好随身物品,提前做好下车准备……
再有一个印象是快要到达沈阳终点站时,列车广播里会响起《沈阳啊,沈阳,我的故乡》的旋律……
绿皮火车平时人不是很多,有时能坐三个人长座上就只有一个人,于是就会有人变座为床,至于觉大的,睡的哈喇子淌上一道也是常有的事。
记忆中,我坐绿皮火车总是赶上很挤的节假日,从老家回沈阳还好说,有送站的家人在车门外那连推带扛的助力,总能挤上去,即使实在不行,也能在家人的帮助下,冒险从车窗爬进去,只不过这些方法,用在从沈阳回老家就不灵了,为了能及时回家,那时需要提前几天到车站排队买票才行。
从沈阳回老家坐绿皮火车有两次我记得最真切:
一次是上班第一年过年,当时单位效益好,发了很多年货,有的外地同事怕不好拿,直接送人或在单位门口的菜市场给便宜卖了,而那时年轻力壮的我则是以肩扛手提的方式,在人群前拥后挤的情况下,爬楼梯,过天桥,愣是把那一堆年货全数带回了老家!
记得那年的年货有:
5升桶装豆油,一盘5斤冰北极籽虾,一盘10斤冰带鱼,一卷5斤冻牛肉,一卷5斤冻羊肉,一箱10斤桔子,一箱24听的罐装啤酒,最最关键的是还一个20多斤的大猪肘子!
记得当时的大件,我是用了两个大丝袋子装好并将袋口扎牢,一前一后挂在肩上,除此之外,两只手也拎了不少,现在想来,就是这些东西,你白送给我,我都拿不动啦!也就是那一次,前来接站的父亲看着我带的那些东西,都有点惊呆了:
“车上这么多人,带这么多东西,就你一个人,你是咋挤上车的?”
还有一次,是孩子出生的第一年过年,本想人多孩子小,挤车实在不便,准备一家三口在沈阳过年,后来听到母亲打来电话时发出的轻轻叹息声,我和妻子改变了主意,大年三十,我们一家三口决定从沈阳坐火车回家,由于没有提前买票,到大巴的火车已经没票了,只能买站票到离大巴最近的新立屯,一路上,车上有好心的大姐让妻子抱着孩子搭边儿坐了几站,怎耐人多嘈杂,孩子一直哭闹不止,后来听说餐车花钱吃饭就可以免费坐到下车,于是一向节俭的妻子和我,破例吃了平生第一次火车餐,我们俩一人一碗面条,孩子坐在餐桌上,那一刻,闻着香味,哭闹不止的小家伙算是安静了下来。
从大巴下火车,离老家还有二十里村路,记得那时我坐家里的驴车多,小毛驴一路小跑,弟弟赶车,母亲和我们三口人坐在车里,如果是冬天,还要裹上棉被,二十里路下来,到家时不但腿脚发麻,那浑身上下,更是因为进屋前后一冷一热,刺挠儿的不行!
成家后,坐绿皮火车回老家,携妻带子,背包摞伞,虽说辛苦,但总是很温馨,尤其是与家人欢聚一堂,看父亲母亲含饴弄孙,喜笑颜开,看弟弟一家其乐融融,所有一切旅途辛劳也就都值了。
2000年,老家安了固定电话,我和妻也有了手机,由此,每次回老家,路上手机总会响上几遍,那是父亲打来的,每次都是一句话:“火车开到哪啦?我是不是该从家开三轮儿去大巴接你们啦?”
2010年,随着生活条件改善,我家买了一辆车,由此,回老家终于不用再挤绿皮火车了,与此对应的是,年近八十的父亲仍会在我们从沈阳出发后,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,说的仍是那句话:“车开到哪啦,就等着你们回家开饭啦!”
写至此处,不禁伤感起来,不为别的,当年回老家时,在门口翘首以待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六年了,子欲孝而亲不待,如今一大家人生活的越来越好了,要是她老人家能看到这一切该是多幸福的事啊!……
后记:
近期回老家,得知随着高铁开通,大巴车站已多年没有客运业务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就连儿时有名的新立屯,在2024年初,也不再有客运业务了,如此看来,绿皮火车怕是要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